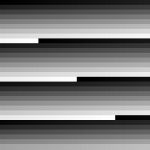藏族姑娘的爱
1

歌声从早晨到下午一直没停过,保持着始终如一的气量、音调,是把好嗓子。守卫赶过七八次,每赶一次,歌声就换个地方响起。歌声围着文工团的大院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,人们心中都有了某种依恋和不舍,他们渴望外出开会的团长赶快回来,把这金嗓子收留。
1953年,这所文工团曾去藏区招兵,想选几位藏族歌手,但一无所获。藏民习惯了在草原放歌,对着牦牛和蓝天抒情多自在,没人愿意离乡背井去当兵。所以,这个女子赤脚从高原一路走到城市,她一定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的。爱才如命的团长在认真听完女子的歌唱后,他决定无论多难都收下她。
女子名叫拉姆,在藏语里,拉姆是仙女的意思。“就你这样儿还仙女?”几个带她去洗澡的小女兵一边拿着刷子给她搓背,一边逗她“喂,仙女,你说说文工团有啥好,你非要来考?你看,你脚底板都走破喽!”
一桶新水哗啦啦冲下,接姆身上的老垢足有两斤多,阻塞了澡堂的下水道,堆成小丘。
拉姆穿上军装,剪了头发,也学别的女兵那样,把蓝色绒线衫的领子翻在军服外,露出脖子。每天早操后拉姆去何老师那练功,“注意气息!”“往上往上!”“鼻腔共鸣!”每天在何老师的钢琴前,拉姆从来没觉得唱歌原来会这么难,她平时站在牦牛背上唱歌,爱怎么唱就怎么唱,唱歌是一件高兴的事。几天练下来,拉姆瘦了一大圈。
但她也有快活的时候,那就是每天去食堂。她在那黑漆漆的食堂能碰到苏俊三次。他跟她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有点不一样了,有点蔫,有点颓废。苏俊的影子小小的,低头沉默地喝汤。拉姆觉得心口那处好疼好疼——一个女子有一个男人没什么了不起,但要命的是,在这爱里掺进了怜惜。
2
拉姆记得那是夏天刚来的时候,她一个人去放牧。远处闷雷滚滚,阴凉来了,她爬上牦牛的背,牦牛背就是她小小的舞台,她开始唱歌。远远的一辆军用卡车停下了,一群兵们下来解手。就在男兵等女兵回来的当儿,拉姆石破天惊的嘹亮歌喉被他们听到了。他们四下张望,寻找声音的来处。拉姆看着那些人,当中有一个小伙子,他从车里取出一把琴。拉姆后来才知道,那叫小提琴。此刻,奏琴的小伙子以他的琴声追上了拉姆的调子,两种声音在暗云滚动的草原交融合拍,拉姆越唱越起劲,那琴也跟着撒着欢儿。
当雨像大豆一样砸下来的时候,解完手的女兵们哇啦哇啦叫着,随着男兵们钻进车里,车开动了。拉姆还在唱,因为她听到那琴声还在!他还在演奏!这演奏越来越近,拉姆发现,那是因为她的脚步正不知觉地向他靠近。
她看清他的脸了,他闭着眼,清秀的脸庞被雨水洗得发白,一头文质彬彬的黑发湿贴住头皮,他的手,他有双苍白而寡欢的手,此时,这手正与那琴难得地缠绵陶醉着。在拉姆18岁的心中,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就那样随着暴雨发芽了。
那大闪电是如何劈过来的,拉姆已经忘记了。她只记得当她苏醒的时候,他正在掐她的人中。他见她没反应,急了。他是真的急了,换了个姿势,他俯就拉姆,捏住她的鼻子,把嘴凑上她的嘴。他冰凉微苦的呼吸涌进她的气管。
她苏醒了,瞪着他。
天已转晴,满天星光,野苜蓿挂着水珠,牛羊沉默聚拢又开始专注吃草。
小伙子对她敬个军礼:“你刚才被雷击昏了,幸好没事,快回家吧。”他走路很快,走了好几百米,他一回头,却发现拉姆正跟着他。她的赤脚走路无声又轻快,这跟随对她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小伙子无奈地笑笑说:“请回吧。”她摇头,摇得又倔又傻,她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说,但此刻,她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小伙子又走了一程,拉姆又跟一程。就这样,山山水水,两人的送别成了相守,一直到天快亮。
“你不能总跟着我了。我要回城里去,我们这次是来招文艺兵的。对了,你唱得这么好,你也许可以试试。”小伙子掏出纸笔写下一个地址,那张纸被雨淋湿又被体温烘干,紧紧地攥进了拉姆手心里。
3
苏俊后来因为迟归队被纪律处罚。他的琴再也奏不出在大雨的草原上那种气韵,他也不知道怎么了,好像无意间丢失了一点什么,又莫名地负担了一点什么。他听说文工团新来了一位藏族女兵,不练功的时候净跑去帮食堂的大师傅搬米、抬菜、扛猪肉。他顺着人们的眼神望过去,吃了一惊——她的脸白净了不少,细看也是个美人。他摇摇头,你还真的找来了,可你来了又能怎样呢,我已经有未婚妻了,在家乡,她等着我回去结婚呢。
拉姆终于在食堂里逮着了苏俊。那天人很少,大家都去看篮球赛去了。她喜气洋洋地坐在了他对面,半点婉转都没有,她说“苏俊,啊却拉噶。”
啊却拉噶,是藏语里“我爱你”的意思。
苏俊一口面条没吃好,有一根从鼻子里喷了出来,拉姆想汉人真是奇怪,吃面条也能吃得这么千头万绪。那天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,连那只铝皮饭盒也忘了拿。拉姆事后往里面装了四个肉包子,把它放在男兵宿舍门口。往宿舍里头望去,空空的走廊很长很远,那是她所不了解的男性的世界。
拉姆把自己打扮成一株会走路的藏红花,红纱巾,红发卡,红嘴唇。
“别跟着我,”苏俊说,“你去好好练声,啊,别跟着我。”
他一直不肯拉下脸拒绝她,是因为他的善良,他不知道,也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善良毁了他本想为之的善良。拉姆跳到他面前,从兜里掏出一瓶酒,“苏俊,你别走,我请你喝酒!”一瓶二锅头就着一袋子五香豆,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。大院后的荒草坡,可以看见很低很大的月亮,苏俊发现拉姆依偎过来了,她的头发因为用了过多的药皂洗了,她很好闻。她说:“苏俊你喜欢我不?”他推开她,让她自个儿坐好。今晚,不论如何,得把话和她讲明白,让她死心。可是,她那又鹿一样美丽的眼睛,那眼睛里的柔情,他怎么好让她受伤。于是,他把本想说的:“咱们不能在一起,因为,我要结婚了。”改成了:“嗯。”
然后她的吻就来了,这个吻也和她的歌喉一样,让他销魂得上气不接下气,领受得死去活来。
4
苏俊的婚假一共是一个月,回来的时候他发喜糖。大白兔奶糖,在那个年代还是上海的代名词,小女兵们疯抢,拉姆也得到一小把。一共五颗糖。在手里攥了太久, 已经渐渐溶化发粘。她剥开一颗,糖纸艰难地和糖分离。糖甜得入骨。拉姆的眼泪流下来。她不能明白,一个对她说“嗯”的男人,一个吻过她的男人,怎么转眼就和别的女子结了婚。
那是新年晚会的前三天,拉姆失踪了。
她在乌烟瘴气的火车站睡了三天,不吃不喝,忘情忘我。她不知道是希望一觉睡死过去,还是想用睡觉把一切想明白。总之,她在第四天清晨醒了,睁开睡肿的眼睛,步行回到部队。此时,文艺兵们都聚集在化妆间里,人们见她回来,也来不及处分她,因为演出马上就要开始,她被按在一张椅上,有人开始往她那睡得鼻青脸肿的脸上化妆。
这是她从没经历过的舞台。这样广阔, 这样排场,又这样深邃。台下是几千名整整齐齐的观众。大家都屏住呼吸,要听这金嗓子的藏族女兵唱《翻身农奴把歌唱》。乐队开始给前奏了,拉姆呆站在那里。两遍过门了,她还是不唱。这时,后台有人主张落幕,让她赶紧下台,别再出乖露丑。可是就在大幕降到一半即将淹没她的身影时,她唱了——
抛开了伴奏,丢掉了话筒,用她本来那腔憨嗓子,用她整个的灵魂,她唱出一首弦子:
一颗麦籽抛空中,期望日月来播种;太阳月亮无姻缘,推说天高难播种。
一颗麦籽抛森林,期望麂羚来播种;麂子羚羊无姻缘,推说林深难播种。
一颗麦籽抛草坝,期望鹿獐来播种;马鹿獐子无姻缘,推说坝冷难播种。
一颗麦籽抛大海,期望鱼虾来播种;大鱼小虾无姻缘,推说海浑难播种。
大幕何时升上去了,伴奏也知趣地停下来。拉姆发现自己唱哭了,然后唱着唱着,她又笑了。就这么唱着,哭哭,笑笑,她觉得好爽快。台下,没有人起哄,也没有人鼓掌,大家静默地听着这藏女的情歌,只是没人知道,她是唱给谁听的。
没有掌声,没有鲜花,拉姆唱完了,自己走下舞台。然后,她一直走,一直走,她发现自己已经走离了城市,走回了属于她的原野。此时,也是夜晚,雨后初晴,星光满天,抖抖袍子上的泥尘,她忽然又快乐起来了。还有什么比回来更好,而且,一切好似如初,只有她知道,她已经深深地爱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