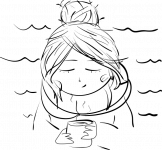新醅酒,谁共饮此残梦
引言:我有新酒一樽,有谁共谱一醉?

序
我叫夏落落,酒艺师,三年前和病体缠绵的母亲移民法国,在一家欧洲传统酿酒坊工作。
在这里,我有很多没心没肺,也不需要知根知底的朋友。每天放工后,就一起去游车河,看展览,跳舞,弹琴,交游……只是,不喝酒。
在这片异国的星空下,我常常在沙滩上发呆。夜还是那个夜,人还是那个人……可,谁能陪我喝酒?
夏之盛放
2005年夏,重庆,气温39度。我坐在孔亮火锅店楼上一间不起眼的单间里,对着面前的一锅红亮的沸腾做最后的冲刺。
孔亮的老板笑咪咪的坐在桌对面看着我,似乎觉得我的表现不错,足已证明他们火锅店料足味浓。一边的服务员也笑咪咪的看着我,脸上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好奇和羡慕,似乎不明白需要老板亲自来作陪的到底是何方妖孽。
其实真是冤枉我,我不是妖孽,妖孽---通常是指那些风情万种,一个小眼刀飞过去就能迷死几百个人的异种---而我,我只是长相平凡的夏落落,这种美称万万落不到我的头上。但,当然,虽然我长相平凡,但我本身并不平凡,因为,我是夏衡的女儿,唯一的女儿。
不过,此时此刻,这间房里确实有一个妖孽,不是我,是他,阿染。
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一年认识阿染的了,就像我想不起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交往一样,大概五年?或者八年?谁记得。总之,这个比花还要美艳的男人,就是我的男人。我在最初受到无数美女白眼后,已经习惯了身边随时随地跟着这么个花骨朵儿,而且偷偷的享受着某种程度的窃喜。
谁让我是夏落落,他是阿染呢。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别人,是羡慕不来的。
现在,阿染就坐在我左手边,正把第四盘肥牛递到我手里,然后继续喝他的冷啤酒。
孔亮的老板再一次把笑脸移到阿染身上:“不知道染少和夏小姐觉得口味怎么样?要不要再来点什么?”
阿染了笑了一下,不过笑里却没什么暖意。他举了举手中的酒杯,忽然说:“没有落落自己酿的好喝。”
孔掌柜略显尴尬,但仍陪着笑,绝没有生气的意思。染氏的唯一继承人和夏氏的掌上明珠来他的店里吃饭,这是多大的面子,有什么好生气的?
我懒得理他们之间的明潮暗涌,生意,哼,永远只有生意,有什么意思?这类的谈话,永远也不会干扰到我的食欲和心情,我只管吃我的好了。
阿染看着我把第五盘肥牛和第十杯啤酒倒进肚子里后,忽然幽幽的叹了口气,说:“落落,你好歹是我奶奶的孙媳妇,不要每次一看到美食就一幅要落草为寇的样子好不好?”
有那么一瞬间,我有点发愣,似乎没有听清楚阿染在说什么。我抠了抠耳朵,又指了指他的嘴,忽然反应过来,尖叫着扑过去:“死阿染!你是在求婚吗?”
阿染用手将我架离他十公分,皱着眉头看我:“那你以为是什么,笨!”
我笑起来,笑的前仰后合,我整个人爬到他的身上,缠着他的脖子,笑的合不拢嘴。
阿染的眼中闪过一丝暖意,却故意冷冷的提醒我:“你要是把口水滴到我的衣服上,我就和你翻脸。”
秋之浓烈
三分之一年后,他真的和我翻脸了,却和我的口水无关。
我应该早就知道,染氏的大少爷,又怎么会为了口水这类小事和人翻脸呢。他陪了这么多年的笑,又陪了这么多年的感情,难道,落脚的,只是这点小事?
可惜,我懂的太迟了。
无穷无尽的鲜花,无穷无尽的香气,还有我亲手酿制的“醉爱”一樽樽被捧到面前。
我的母亲和阿染的奶奶笑咪咪的看着我,一边夸我漂亮,一边用左一层右一层的珠宝将我点缀的更加夺目耀眼。
我傲然的接受她们的好意,是的,今天,我是主角,再风光,再嚣张,也是理所应当。我刻意的忽视了奶奶眼中那一闪而过的不耐,以及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居然没有到场的父亲。我的幸福,由我自己作主就好,不是吗?
母亲说:“今天只是订婚,等你父亲回来主持正式的结婚典礼,一定会比今天更热闹。”
奶奶连忙接口说:“那是,我们染家就这么一位孙少爷,夏家也就落落这么一颗掌上明珠,再怎么,也要映红半边城才像话。”
我得意的笑着,隔着纱帘看不远处耀眼的像星辰一样的阿染,又望望镜中难得显出一份娇媚的自己,心满意足。再想到今天众星捧月般的自己,也有从云端跌落的那一日。
订婚仪式非常的顺利,阿染远在加州的父母和我的父亲都发来贺电。双方企业的各种关系也纷纷给足了我们小一辈的面子,皆大欢喜。
当阿染将订婚戒指套在我手中,当司仪端了两杯“醉爱”让我们饮尽杯中酒时,气氛达到顶点。星空下,酒香中,我,醉倒在阿染怀中。
在醉倒的一瞬间,我似乎在阿染眼中看到一丝恍惚。我想问他,却发现已经不能支撑自己身体的重量。“醉爱”杯中物,最爱眼前人,真的很,醉人……
冬之萧飒
我不懂做生意,也不懂做家务,可我会酿酒。每次当我捧着新酿好的酒送至阿染唇边时,都会在他脸上看到一丝极其满足的微笑。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,我几乎认为,与其说阿染爱上我,不如说是爱上了我的酒。
可是,这有什么呢,我就是阿染的酒,不是吗?
我们对酒唯一的识别差在于,我最喜欢的是订婚宴上的“醉爱”,他却喜欢我为他特别酿制的冰啤“绝晴”。他说那种冰如冬,冷静如冬的感觉才像他。
我斜睨着他笑,像他吗?才不,他是花一样的人,温和而优雅。是温室里的名贵花种,哪有一丝寒意呢。
阿染看着我,说我不懂他。
我不懂他?
托盘上放着一只翠色琉璃杯,里面是我新酿的酒,这酒叫“花”,是我送给阿染的礼物。酒味是层叠的花香,一瓣一瓣的绽放,无比香浓诱人。我想,他一定会喜欢。
此时正是午后,冬日的阳光虽然不那么温暖,却也有一些明亮的感觉。阿染在书房与他的父母通电话,我蹑手蹑脚,不想打扰了他。
忽然,走廊里吹来一阵冷风,不知是谁把朝花园的窗户打开了,寒风一阵阵吹了进来。
我皱皱眉头,正要去关窗,忽然听到书房内阿染一声压抑的怒吼,不由停住脚步。
阿染的脾气一向很好,对父母更是恭顺有加,什么事,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?
“不行,刚订婚!落落并没有做错什么!”
“她长相普通您也不是第一天知道!夏伯父有私生子与她有什么关系?难道这个错要算到落落身上?”
“继承权!继承权有那么重要吗?”
“父亲……我和落落在一起九年了,九年了……”
“父亲……”
“我承认,我只是爱上了她酿的酒,可是,这世上,有几个人,可以陪我放心的,尽兴的,喝酒?”
“父亲……”
“是的,我明白。”
我静静的站在走廊,像被传说中的武林高手点了穴,任由阿染断断续续的声音飘进耳中,脸色苍白,宛如鬼魅。
母亲被人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时,已剩了半条命。我扑上去,抓住她的手。她的手苍白,没有一点血色,往日的精神不知去了哪里。
我紧紧抓住她,盯进她的眼睛:“妈,这不是真的。”
可是,母亲的眼睛中是灰蒙蒙的一片,没有焦距,就像一棵失去灵魂的枯树。
我不肯放手,死死抠住救生床,不知能说什么,只是盯着母亲。
一只冰凉的手把我从地上拉起来,我扭转头,眼光在碰触到身旁的人时,瞬时凝结起来。我问他:“你来干什么?”
他长时间的沉默,似乎在思考怎么开口,有那么一瞬间,我几乎相信了他的勇气,我瞪视着他,怀抱着我最后的,破碎的一线希望。阿染,却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,只是缓缓的放开了我的手。
我心头一阵悲恸,阿染,就这样放手了么?虽然,我们没有惊心动魄的誓言,可是,九年了,九年了,就这样了么?
春之复苏
古代的男子似乎到了十二岁会有一个成人礼,小小的男生戴着高高的成人礼冠站在众人面前接受祝贺。男生的父辈,要郑重的当着天下人的面,宣告一个小男子汉的成人。从此,那男生变成了一个男人,享受一切世间赋予男人的特权,继承权,荣誉以及责任。
父亲在他的私生子满十二岁时,用残酷的手法,为那个小小男子汉举行了他的成人礼。
而我与母亲,是他成人礼坛上的祭品。
母亲自杀未遂,三个月后,与父亲离婚。
我,夏落落,丧失了夏氏的继承权,在众人眼中变成了一介平的不能再平,凡的不能再凡的普通女人。当然,与此同时,我失去了阿染。或者应该这么说,从一开始,从九年前的一开始,我就从没有哪怕一瞬间真正拥有过阿染。阿染是朵花,这花没有根,他走向,握在染氏的当家人手中,他们说要他东就要东,他们说要他西就得往西。
阿染的一切光彩都来源于染氏的辅佐。当我还是染氏的利益目标时,当然,那朵花就是我胸前最美的装饰。但,当我一无所有时,那只拿花的手,自然会将他毫不留情的从我身上拔走。
无所谓我悲不悲伤,无所谓花悲不悲伤……
我沉沦了一整个冬季,每天泡在酒库里。醒了喝,喝了睡,睡了醒,醒了再喝。有时喝的吐了,也不去理它,理它做什么呢?我这个人都是被人喝到肚子里又吐出来的残酒,何况其它?
直到那一天,那是一个大年夜。我从昏睡中醒来,看到的,却不是一如既往满地的酒渍,而是---一地的鲜血!
母亲第二次入院急救,我呆呆的坐在急救室门口,看着护士将一袋袋血浆流水般送入房内。心脏,忽然的,就那么跳了一下。
像有人在我胸口里拿着一把铁钎,向上,轻轻一捅。
我疼。
疼到我想起很多事,也疼到我忘记很多事。是的,还不清醒吗?这么多年的众星捧月,幸福满溢,并不是落在我身上,而是落在父亲的女儿身上,如今,我已被父亲抛弃,除了母亲,我还剩什么呢?难道,还在希冀奇迹突然发生,阿染回转头来吗?
眼泪,冰冷的从我眼中掉落。
落,落,落落……我,醒了。
镇静的站起来,苍白的脸上虽仍有不健康的遗迹,但我的心,开始了自由的跳动。我找到医生,找到护士,拿出我与母亲的所有积蓄,我说:“请救活她,无论如何,请救活她。她是我在这世间唯一的亲人,谢谢您。”
从出生至那刻起,夏落落,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谢谢。她所有的幸福美满富贵快乐都是与生俱来的,都是理所应当的,都是不需要思考的。当她终于明明白白的说出谢谢那两个字时。她终于从云端里走了下来,变成了一个凡人。
而我,重生了。
尾声
奥马拉海滩暖暖的阳光洒在我身上,金黄色,有一点点刺痛,但至少让我明确的感觉到我还活着。
活着就好。
母亲住在离海滩不远的一家疗养院,费用不太高,我目前的薪水足以支付。哦,对了,我已经加了薪,在这个酿酒坊里,我是薪水最高的东方人。
我为酒坊酿了一种酒,叫“花”。到今天我都记得,这酒酿出的第一天,所有人是怎样的欣喜若狂,他们说,这是人间极品的味道,那层层叠叠溢出的香,像一枚瓣瓣绽放的鲜花,香的浓烈,香的无羁,香的动人心肠,唯一的问题,是酒的后味有点苦涩,像盛放而衰的花圃,再无一点春色。
听着这一切,我只是微笑,是吗,像花吗?苦涩吗?也许吧,谁在乎呢?
我没有喝过“花”,你知道吗,没有人,能陪我喝。
后记:若你以为生离死别才叫爱的伤害,若你以为海枯石烂才是爱的真谛。那么,你错了。也许你面前那一叶憔悴的海棠,已受尽了爱的磨难,但你看的出吗?也许你在路边看到的小贩已在爱海里九死一生,可他脸上,有半点痕迹吗?千帆过尽,留下的,也许,仅仅是,孤单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