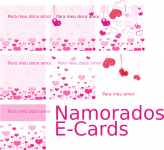梦醒,起身见泪痕
题记:爱情哪来那么多浪漫?哪来那么多刻骨铭心?在真实的世界里,只能感受到最真实的爱。我写的,只是那般真实的爱恋。

「一」
有人说秋天是个健忘的季节,而且不知谁定义的说,秋天是个分手的季节。黄叶飘下,流水潺潺,如果此景又是发生在傍晚时分,那么配着黄昏的情调和争吵不断的恋人分手不失为一种恰当的选择。庄户人在秋天能收获一堆谷物,而貌合神离的人,在秋天只能收到一句挖心窝的话。但造成秋天成分手黄金季的主力军,并非那些不谙世事青春男女,而是那一堆拿着简历四处求职的大学生们。
天木在前一天的晚上再次失眠,这次不是因为失败的面试,也不是因为爹妈催着回家的电话。虽然他确实很讨厌被拒绝的感觉,也不愿意听那对老家里的父母唠叨没完没了。不过这些在目前的形势下似乎都是能放一放的。按照天木自己的话说,老子和美国一样,先收拾完伊拉克在考虑伊朗和朝鲜。工作和父母是伊朗和朝鲜,而蓉艳,就是那个伊拉克。天木一晚没睡,逼着自己组织语言,该让自己怎么告诉蓉艳利害关系和未来前途,以及让她理解什么叫当断不断,越理越乱。不过这话怎么说都说不好,而且自己越说变得越耸。为什么?因为他想彻底的拒绝一个心爱的女人和一段深厚的感情,割舍这些不像手术割掉个器官那么简单。肉体疼痛怎能与那个容下一江爱水的心海比呢?
但天木不愿意因此打乱自己的计划,喃喃的说了句:“怕球呢!爷们儿该了断就了断。我又不是李煜、柳永,整那么婉约干什么?有话直说,睡!”,于是埋头枕边,卷着被子,换了个舒服的姿势一动不动。由此可见,有时候男人是无情的,而且大部分时间男人不仅无情而且绝情。可你再冲着他的心深挖一锹,翻出来却是浓浓的深情。男人要装,会装,至少在哭哭啼啼的女人面前不能抢过手绢自拭泪水,那样怎能叫做男人?做个负心汉比痴情男要好很多,至少在男人观念里,通常都是这么认为的。天木竟这么睡去,死死的睡去。他从不信想一个人的话能在梦里见到她,那些男人清晨打电话给女人说,昨晚我想你想的梦到你了。那纯属男人扯淡,相信这鬼话的女人是笨蛋。要记住,没有一个人能让你翻来覆去的在跳跃式发展的梦境里存在多久的,如果有,也只是一瞬罢了。别以为你会成为你所爱的人梦里的主角演个五十集的电视剧,你在梦里出现的,只是那么一瞬,就像每个三秒换个图片的幻灯机里的图片一样,就那么一瞬,仅此一瞬。
「二」
见面还是在那片点缀石椅石凳树林里,叶茂阴凉,只是初秋来的时候让一些逞强在外照耀的绿叶染了一圈淡黄。这里充满过两人的欢笑,充满过两人四年最甜蜜的回忆,也充满过曾经争吵咆哮,树木都是见证者,这次它们又要见证一次,这次之后,不知道会不会有下一次。天木选择这个地方并非有意,也不是想像言情剧里一样让那个女孩走的时候伴着过去的点滴,只是,他打电话给蓉艳,就一句话:“老地方见。”老地方,多可怕的一个地方,地方如同女人的容颜一样,新鲜的总是好的,至少会有过多的惊喜。可一旦老了,没了感觉,没了兴奋。只是在熟识的地方坐到熟悉的凳子上,等着对面的那个快没了感觉的人开口,一问一答,好似法庭辩论一样。今天,天木是会先开口,他要说的,就是他一晚上都没组织好的那点词句。
蓉艳准时到达,不差分毫,虽然她还有很多毕业的事情要忙,但是,最后的一段时间,她还是很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机会,见一次少一次。虽然蓉艳用情很深,但是她也似乎感觉到了些什么东西,亦或说不上感觉,只是看到现实而已。她想到了这一天。早已想到了这一天。坐在她熟悉的位置,献上他标志性的微笑,虚寒了几句,天木也随便应答了几句。同时沉默,死一般的沉默,沉默到能听到旁边艺术专业学生唰唰的作画声。怎么形容?尴尬?还是悲默?反正两人都不抬头,扣着自己手指,然后扣指甲盖。人最不能忍受沉默带来的那种撞击所形成的痛,天木调整着身体角度和两条腿的摆放位置,只为让自己舒服点,然而包裹着沉默的人,舒服只是束缚。终于他清了清嗓子,“哼”了一声,准备着。蓉艳看到天木的不自在,自己也加快了抠手指的速度,还微微颤抖。她知道,来了,终于来了。躲不开就是躲不开,像《死神来了》一样,命绝子时,绝不丑时收尸。
“我们…我们算了吧。事到如此,我即使千百个不愿意,但也实在没办法,我作不了那么多,也达不到要求。希望你理解。”声音和身体都颤抖着,像共振一样。勉强的笑了笑,以掩饰他哽咽的声线,不容蓉艳发觉从心底泛起来的疼痛。天木说了,说的还算条理清晰,这也许是天木做得最大最果断的决定,只不过,代价同样巨大。读不懂天木的笑属于什么类型,想掩饰什么?还是装着心宽无所谓。或者,那就不是笑,是没眼泪的哭。
蓉艳抠手指的手停下了,啜泣起来,但没出声,不用出声。心理准备已经做好,只是真临到眼前,总是忍受不了。她把头弯向一边,还是努力控制不让自己的泪整滴的滴下来。也许,这是她的回应。
老天要是赏光在这个时候刮来一阵轻风,吹落点那些梢头的黄叶,飘摇在两人面前的台案上,或者划过滴下泪水的眼旁。这太浪漫了,也太琼瑶了。可是,真实就是真实,没开花的果不会成熟,没过秋的叶子不会落掉。即使你撕心裂肺,树枝和叶片联系依然紧密。哪来那么多浪漫?没有,统统没有。
「三」
遵照父母意愿,天木回家了,他不是不想留在那个假装繁华的城市里,只是,男人有时候也需要个避风的角落,躲开一些不想触摸的实体。于他来讲,家是个好地方。工作不怎么好,但也算温饱无忧。而且不累,坐坐椅子,聊到傍晚下班,月末领工资。生活平淡无奇,问题总是有的,但是不再像当年解决伊拉克和伊朗、朝鲜一样的紧迫。爸妈还是吹促着赶紧找个姑娘成家,有家是舒服的。可天木认为,家和当年的沉默一样,不是舒服,而是束缚。不愿与他接近。父母没办法,儿子大了和长大的狮狼一样,放出去就别想着继续管着他的起居。
一天天的过,一天天的平淡,如果不看新闻他甚至会觉着这个世界是不是停滞了?百无聊赖的人会感觉世界辜负了作为人类载体的价值,恨不能天天火山灰、沙尘暴。天木就这想法,他想自己开着自己那辆赞了两年钱买来的二手思域像《2012》一样载着家人逃难,可是与之相比,他所缺少的是一个妻子,准确的说是前妻,以及一个情敌。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,在死亡面前,人心竟然能容得下过去想千刀万剐的情敌。
挨到下班,打卡走人。等了若干个红绿灯和点了几十次刹车,天木回来了。回到那个百十平米的监狱,他这样比喻自己的房子,除了出入比较方便,其他与监狱无他。今天门口的信筒竟然多了一份信件。天木盘算,没到月末怎么会送来吹款单?难道是上个月的?打开之后,展了五六次才彻底展平信纸,信纸头上画着的喜洋洋和灰太狼证明这不是吹款单。他扫视第一行字,呆住了,准备锁车的他练遥控器都没再按下去,信头的昵称,已经两年没人那么用过了,而两年之前,也仅仅一个人用。他看不下下面的文字,虽然是黑字,但是好像突然泛白,无力的落在打着横格的信纸上。再一次泛起来的,他不能形容,多少有点欢快,多少有点痛心,多少有点,五味杂成。
天木坐到沙发上,像软泥一样。开瓶可乐,提了提神他跑到电脑前,想在那几个群里找到已被删除了好友的蓉艳。甚至连开心网都打开,想用下高级搜索。但鼠标和键盘似乎被封闭起来,他始终没按下去。期间几个单位同事约他出去喝一杯,可收到信的他一概拒绝。他所纠结的是,该不该再次翻开这封尘封已久的装满回忆的瓶子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是蓉艳会时隔两年再来找他,也不知道这封信是什么意思。可是,几行字和那个昵称让他的死灰里隐约出现火星。
电话响了,打断了他的思考,他接电话看了下电话上的电子钟,11:48了。电话那头没有“喂”而是直接的一阵坏笑,笑的差点把电话听筒变成吹风机。天木把听筒拿开耳朵,等着那边那个人正常了再听他说话。终于,那边的人不再笑,只是问,信收到了吗?这人是刚刚约他喝酒的同事。天木晕晕乎乎的想把信和这个说话的同事联系起来,但是不能,同事继续说:“哥们,别抑郁了,出来喝杯吧,那只是玩笑,让你过个开心的4.1”。
天木生气的摔了电话,摔得稀巴烂。没想到这些仅是这群无聊的人的一个玩笑。但是那个变形的电话再次响起了铃声,天木呆呆着不想接,不想听那群人解释。可是一直响,一直响,三分钟了都没有停。他终于忍受不了,抓起那个电话听筒,大声咆哮,谁啊你!再玩我宰了你!电话呼呼作响,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,是我,我是蓉艳……
“轰”一声,天木蹬倒了床头的闹钟,他急速的起身,听着那边掉地的闹钟不停的作响,摸着自己头上淋漓的汗水,他的枕头上湿了一块,是泪?还是汗?这,只是一个梦。